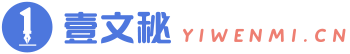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
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新鲜出炉,张晋藩事迹是什么样的呢?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4年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(通用5篇),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需要带来力所能及的有效帮助。

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精选篇1
张晋藩坚持教育事业最伟大之处就是培养人才。古书中常有三句话:“兴礼乐、建学校、树人才。”我总感觉到当今世界的竞争,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。作为一名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,我将继续尽力将所有为学、为人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,希望培养更多党和国家需要的优秀的法治人才,使“后继不乏人,后继更胜人”,为全面依法治国做出更好的贡献。同时,我也希望广大教师、各行各业都努力培养各自领域的专业人才,让中国培养的人才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,有所担当,有所作为。
少年强则国强。我当年组织编写《中国法制通史》《中华大典·法律典》和《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》的时候,既邀请了老一辈的专家,也吸纳了大批博士生和中青年学者。后者经过历练,大多成为编著上述图书的主力军和推动中国法制史学发展的生力军。我希望当代的青年学生们,戒骄戒躁,甘于下真功夫、苦功夫,甚至笨功夫去做好学问,切忌避难就易,人浮于事。同时,我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,发扬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,弘扬忠诚、执着、朴实的英模品格,努力发展成才,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。
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精选篇2
为国家富强而读书,是张晋藩从小立下的志向。
“1930年我出生在沈阳。我的童年是在伪满洲国殖民统治下度过的,那时历史课不教中国的历史。”张晋藩回忆道,“‘灭人之国,必先去其史’,侵略者就是要让中国人忘记自己的根。”
“祖父因饥荒过世。战乱频仍,想买一口棺材都没地方买。幼年时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,激励着我要为国家富强好好读书。”张晋藩说。
1949年7月,张晋藩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,此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。当初,在不少老师和同学眼中,资质出众的张晋藩就读冷僻的法制史专业有些屈才。但是,在酷爱读书尤其是爱读史书的张晋藩看来,这个选择真是天大的幸事。
“观今宜鉴古,无古不成今。中国古代法律的内容精彩纷呈,传承中华法制文明,可以弘扬中华民族在法制上所体现的坚韧进取的民族精神,激发中华民族的自信心、自豪感和内在的潜能。”张晋藩说。
1979年以前,国外曾三次召开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,都未邀请大陆学者参加,这严重伤害了包括张晋藩在内的中国学者自尊心。
张晋藩说,必须要加快编辑出版《中国法制通史》,不能让子孙后代到外国去学习中国法制史。
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精选篇3
张晋藩:改革开放前,除个别学科外,我国的学术研究交流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,中外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缺乏基本的学术交流。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,各种学科学者纷至沓来。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制史学的代表,在1980年前后几次接待了很多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外国学者。
从谈话中我了解到,1980年之前在国外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的国际研讨会,却多由日本学者牵头担任主办方,且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。彼时,西方国家法律史学者济济有众,成果斐然,日本和美国俨然成为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。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,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做出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与贡献。诚如美国学者蓝德彰教授坦言:“我们不知道有哪些有影响的中国法制史著作,当然也就无从知晓中国学者的状况。”
中国是中国法制史生生不息的摇篮,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却没有建立在中国。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,对他们的成果应予以重视。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,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。20世纪30年代,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,付出了极大的努力,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面对尖锐的挑战,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,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,岂不是一种罪过?为恢宏法律史学界的志气,我召集当时国内法律史学界几乎所有学术力量,筹划编写《中国法制通史》多卷本,力图借此把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。这是时代的需要、法制史学发展的需要,也是中国法制史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。
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精选篇4
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,张晋藩留校任教,从此在中国法制史研究和教学之路上辛勤耕耘,不断开风气之先。
除了《中国法制通史》,张晋藩牵头历时23年编辑出版《中华大典·法律典》,耗时16年出版《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》,发表新中国涉及古代民法第一篇论文,撰写《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》《中华法制文明史》等享誉学界的著作60余部,主编《中国司法制度史》《中国民法史》等30余部专著和20余部教材,发表专业论文430余篇,其部分专著和文章已被译成英、日、韩等多国文字出版。
尽管著述等身、载誉天下,但张晋藩始终恪守“不偷懒、不自满”治学原则。
“对于一些发表过的文章,时不时重读一下,看看是否要修改。”他说,“什么时候也不敢说一句狂话,自己只是看到法制史殿堂的门楣,载欣载奔而已,距离‘达到’还远着呢,因此也不敢偷懒。”
由于长期的辛勤劳累,加上年龄不断增长,如今张晋藩的视力严重下降。但是,借助高倍放大镜,他仍然每天上午八点半开始工作,坚持阅读写作、指导研究生论文。
“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,完成这些项目,就是为了发展中国法制史学,弘扬五千年的中华法文化。”张晋藩说,“我深切感受到,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,没有自己强大的文化支柱,一个国家就很难全面发展、真正强盛。”
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精选篇5
1954年8月6日的《光明日报》,竖版繁体,本报记者也是第一次看见。《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》一文是头条,显眼。
这是张晋藩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,那时他24岁,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,留校任教。那一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,宪政研究成为他进入学术领域的门径。“当年研究宪政是热点,但后来这成了我一生的研究课题。”从他的著作年表中勾出和宪法史相关的成果,是一条纵贯60年的直线:1955年《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宪丑史》,1979年《中国宪法史略》,2004年《中国宪法史》。这是指著作,相关的几十篇论文不包含在内。
与这条线平行的,是民法史、刑法史、行政法史、监察法史等其他专门法史的研究脉络。当年国家法制草创,每一项努力都是在填补空白。而现在,这些勾画在28页A4纸上纵横交错的目录,构成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构架。
最难的是法制通史的撰写,时间上要上溯到上古的氏族战争,门类上要包含刑法、民法、经济法、军事法等等诸多项目,每一项都涉及到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集纳提炼。这是学术上的“难”,更难的是组织工作,一项大事,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一时难备,都是问题。
张晋藩决定挑战这个大部头。那是1979年,中国学术界春风回暖,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,他遇到了美国学者兰德彰。对方告诉他,在1979年前,国际上已经组织了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,但从未邀请过任何大陆学者参加。美国学者的语气带着遗憾——他们从来不知道中国内地还有张晋藩这样的法制史学者,也无从了解大陆的学术研究水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