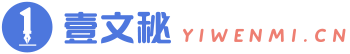呐喊观后感1000字左右
在《故乡》中主要写了鲁迅回老家变卖房屋的事情。此时的鲁迅已经二十多年没回故乡了,但正如他所说,此时的故乡毫无生气,他的心情也不大好。但鲁迅就是鲁迅,写这种回忆型文章也植入了批判封建社会的人精神的伤害。《故乡》中的这种人物就是闰土。
第二日,我便要他捕鸟。他说:“这不能。须大雪下了才好。我们沙地上,下了雪,我扫出一块空地来,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,撒下秕谷,看鸟雀来吃时,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,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。什么都有:稻鸡,角鸡,鹁鸪,蓝背……”
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。
闰土又对我说:“现在太冷,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。我们日里到海边检贝壳去,红的绿的都有,鬼见怕也有,观音手⑤也有。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,你也去。”
“管贼么?”
“不是。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,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。要管的是獾猪,刺猥,猹。月亮地下,你听,啦啦的响了,猹在咬瓜了。你便捏了胡叉,轻轻地走去……”
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猹的是怎么一件东西——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——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。
“他不咬人么?”
“有胡叉呢。走到了,看见猹了,你便刺。这畜生很伶俐,倒向你奔来,反从胯下窜了。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……”
少年闰土和鲁迅如亲兄弟一般,在一起什么话都讲,什么有趣的事都说。但这二十年间,封建礼教对闰土的精神进行了摧残,让他的脑子里出现了等级制度,人人不平等,便出现了二十年后的的悲剧。
这来的便是闰土。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,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。他身材增加了一倍;先前的紫色的圆脸,已经变作灰黄,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;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,周围都肿得通红,这我知道,在海边种地的人,终日吹着海风,大抵是这样的。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,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,浑身瑟索着;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,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,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,像是松树皮了。
他站住了,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;动着嘴唇,却没有作声。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,分明的叫道:“老爷……”
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;我就知道,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。我也说不出话。
这是中年闰土的形象,非常穷困,身上只有一件极薄的棉衣。农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,社会的压迫,让这些本身就穷苦的农民变得更穷苦,日子更难过。20年的劳苦生活让那原本可爱的、充满活力的、和鲁迅称兄道弟的闰土消失了。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的描写形成了很大的对比,称呼从“迅哥儿”变成了“老爷”,更是让人觉得心酸,并为闰土感到悲哀。从闰土这个活生生的实例来批判封建社会对劳动人民的迫害,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,封建礼教对劳动人民精神的摧残!
呐喊观后感1000字左右篇2
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接触鲁迅的文章,才会真正感觉到“大文豪”的文豪之气所在。薄薄的《呐喊》中虽然只有十几篇文章,但不乏经典之作,如其中的《狂人日记》和《阿Q正传》。一部作品或者一篇小说能经历时光的筛选和磨炼,然后流传至今,思想的光辉丝毫不褪色,那应该是其中的内容更多是表现出深层次的意义,而《呐喊》正是如此之作。虽然鲁迅先生早已作古,但其文笔文风仍不是活力,而在《呐喊》中对国民性赤裸裸的剖析和抨击,在今日看来,更有另一番风采。对中国国民性的抨击,不止是鲁迅一人,像林语堂、柏杨之辈,也对中国的国民劣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但与他们所不用,鲁迅的《呐喊》更对国民性“劣根”的“根”进行剖析,从整体的民族性入手。一个民族“国民性”的形成,自然与几千年来文化的潜移默化的熏陶有密切联系。几十年前,我们的国民性如此,今日,或者几十年后的今日,“我们”或者“他们”也会如此,劣根犹存,这边是国民性的“根”。
鲁迅曾说,他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。不可否认这与当时国人思想钝化,麻木不仁有关,而这一切的形成又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。他在《呐喊》中对整个国民性进行猛烈的剖析抨击时,其实也就是在对自身的剖析和检讨。正如其中一文所说的那样“人性大抵都如此,只不过是个人控制能力不同罢了”。
从《阿Q正传》中,更能明白鲁迅文笔的不朽,或者说是阿Q的不朽。其实阿Q一直都没有走远,也许就活在我们自己的身边,甚至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身,或许我们不愿承认罢了。鲁迅用浓墨描写阿Q的同时,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在“借鉴”自己或身边的人。而阿Q发明的“精神胜利法”,更是我们中国国民性中的“精粹”,也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得以借用的“秘籍”。看看我们以前的“天朝上国梦”,看看我们现在还把自己得不到的当作是对别人的赏赐,斗不过别人,便躲在自家的被窝里显耀祖宗的余威,就算在睡梦中,嘴角还露着轻轻的轻蔑笑意的痕迹,俨然一副阿Q标准像。
读鲁迅的书,尤其是呐喊之类,读多了,每次都有心惊胆战的感觉,甚至有时还会有冷汗直冒,模模糊糊中似乎是在隐射到自己的“劣根”,时不时总要抬头环视四周,看看别人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异样。
之前曾经看过一篇关于评论鲁迅的文章,大体是说鲁迅在猛烈抨击国民性的“劣根”时,国人看了隐隐约约“知其所指”,但又不会感觉“害怕”,那是因为这种劣根早已根深蒂固,四海皆是了。你如此,我亦是,他一样,既然大家都如此,那怎会有“害怕”呢?
在国民的迷茫中,鲁迅大声疾呼,奋力呐喊,只是他那薄弱的声音有几个人会听到呢?听到的人之中又会有几个明白呢?而明白的那些人又会有几个去改变呢?
也许,更多,更多时候,都自己在无力地呐喊。